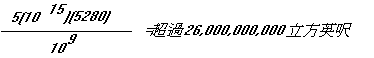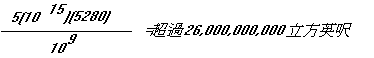记录历史不正确
那仍然留下的问题是,实际记录下来的历史是否与乌社尔年代表相冲突。鉴于在所有实际测定年代方法中许多无法证实的假设,对人开始记录年代之前的任何年代,就永远不会有确实的把握。并且,由于人喜爱夸张,就是这些记录,也并不都可靠。
一般说来,最古老的两个文明,埃及及苏美人的文明,是我们已接受年代的根源。 『当然,史前的发现,因其性质,未伴随任何写下的记录。唯一可能有的资源是从已知找出未知。设法从有历史记录的埃及美索布达米亚历史文化向没有记载的周边探索。
比如,那以古代记录为基础的埃及历史年代,可以没有甚么问题的延伸到主前1900年,因为,记录中有天文的事件。因此,埃及的『帝王表』,虽然不是那么样使人完全放心,还可以用为建造成另一个再向前推十一个世纪,至主前3000 年的年代表。』注三三 这个年代,主前3000年,离乌社尔所算出的洪水年代不远。埃及第一个王美尼斯的年代,很可能与挪亚的孙子麦西时期相当。他可能是埃及国的创建者。(麦西这个名字在圣经中与埃及同义,曾十几次如此使用过)。
但是埃及的开始,及其它国家的开始,其年代必须从巴别塔人分散之后开始计算,依照圣经的说法,那是在洪水之后100年。 麦西,他的父亲含,可能在人分散之后,仍然活了一段长时期,因此,许多人用了相当长时间迁移到尼罗河,在那里奠定了立国的根基。埃及在圣经中也称为『含地』诗106:21-22
埃及长久分为两个帝国,上埃及,与下埃及。上埃及称为巴忒罗, 显然得名于 创世纪 10:14节,麦西的子孙帕斯鲁细。下埃及则继续与麦西本人相联。上面所提到的帝王表,尤其是曼内托的年代表(Maneto-约在主前290年)提供了埃及年代表主要的基础。而埃及年代表又成为发展其它古代国家年代表的基础。但是,有些迹象显出,他的年代表中包含了两个帝国同时代的王朝,而将它们的年代错误的加在一起。而且,曼内托历史所根据的数字,很可能得自早期帝王及文士们的夸张说法。因此,埃及第一王朝的主前3000年,应该大为减少。
同样的问题,可以放在苏美人的帝王表及年代记录上。在巴比伦,吾珥,基什,埃卜拉及这个区域其它城邑的最早的王朝,显然是在埃及第一王朝开始之时同时开始。一些学者相信,如像埃及的情形一样,可能类似的力量也在作用,使其扩张了几百年。
无论情形如何,实际年代记录的开始,不超过主前三千年。并且这些年代都可能是夸张的年代。寇飞利(Donovan Courville)注三四与费里可夫斯基注三五以及一些其它的学者,曾提出使人信服的理论说,这些古时的年代,都应该至少减少八百年。 这样,认为乌社尔年代表中洪水年代为主前2300年左右,是十分容易辩护的。
但在另一方面,许多基要派圣经考古学家辩称说,洪水的年代是主前是3500至4000年。这不仅是因为如帝王表,放射性碳及年轮测定等原因,也因为通常所定主前2000 年亚伯拉罕时代人所居住复杂世界的缘故。 许多保守派圣经学者提倡说,在创世记第十一章的族谱表中,可能有一两个间隙。比如在路加福音 3:35-36节与创世记十一章平行的族谱之中,该南的名字插在亚法撒与沙拉中间。那最可能存在着大间隙的地方是在法勒,『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创世纪 10:25十一章中所列出法勒之前三个人的寿命是438,433,464岁,法勒及他的两个孩子的年龄则是239,241,230岁。因此,在寿命减少了一半的法勒与希伯之间,可能有一个长的间隙。
在法勒与希伯之间是否有,比如说,1500年的间隙呢?在这种情形下,创世纪 11: 16节,就可能译为:『希伯活了 430 年,生了法勒 (的祖先)。』在那个时代,这个间隙代表四五代人的寿命。这个长时期沉默的理由可能是因为巴别塔语言混乱,使记录中断所造成。这样,当法勒不知名的父亲过了一千年之后再继续记录 (在法勒的祖先希伯的儿子诞生之后,四百年闪去世之时记录中断) 之时,他为他的儿子起名法勒,以记念巴别塔悲惨的背叛及其后果。
这种说法是否合理,读者可以自己去衡量。是否要效法寇飞利与费里可夫斯基重新解释历史及考古学资料,以符合乌社尔年代表,也仍然是个争论中问题。无论如何,根据这些解释,使圣经年代及历史文化考古学年代彼此符合,诚然是可能的。进一步的研究应该可以解决那一种解释才是正确的问题。
文明之前
这样,圣经的人类早期历史,已充分得到新石器时代及其之后的考古学实际资料的支持。但是,对旧石器时代及中石器时代呢?那些旧石器时代的人,尼安德塔人,直立猿人,克罗麦格兰人呢?那些美国印第安人,南海岛民,爱斯基摩人,非洲的矮人,并其它被认为是原始民族的人呢?他们如何去到海岛,森林,北极及深山中的呢?
进化论的人类学家常说,在较低之处找到了石器时代的文明,甚至在较高之处发现较进步文化的文明同一地点发现。对他们说,这是讲说人类的进化。 但是,对这些资料,还有另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充分与发现的资料及圣经相吻合。洪水是普世性的,并造成极大的灾难。彼得说:『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彼后 3:6所有洪水前的人及他们的文明,都被水淹没,毁灭,摧毁,世上没有任何地方留下一个城市及村庄。
因此,若有任何人的骨头或人的制品被保存下来,它们就几乎必然在流动的沉积中深深地,任意地被埋葬,使其以后不容易发现。人常问,若是洪水毁灭了洪水前的世界,为何我们没有发现更多的人类化石?实际说来,因为在洪水前,各大陆与诸海洋的地理情况与洪水前的完全不同,许多洪水前的人类尸体可能现在深深埋在海底的沉积之中。另外的一些可能深深埋在地壳的岩层里。但是,由于人的机动性,大多数洪水前的人,或者完全未被埋葬,是最后被水淹死,在地面干了之后,尸体分解了。
但是,为了辩论,我们可以假设,有十亿人被埋,在洪水的沉积中变成化石。地球的表面面积约为5x10的15次方。平均的沉积至少是一英哩厚。(5280英呎)因此,平均埋葬一个人的沉积容积为: